[一]
写的是一个叫文的校园诗人的经历,和经历中的辛酸与美丽。
[二]
也不知有多少载的积淀了,每个春意正酣的四月,这个校区里的成熟而略带几分傻气的大四孩子们,总是听着了塘里的蛙声就开始疲于图书馆和宿舍这两点之间。岁岁如此,且不问是哪届的孩子们为我们结的缘,算而今已是一声温馨的提醒了。
今年当然不会例外,我们也有幸赶上了这充实的一拨。查资料,绘图表,总结,疏通文字……忙是忙了些,可四年来的蓄势为的也不就是这一朝的待发吗?再了,许是一辈子也就只写这么一回学士论文,怎么说也该算是“终身大事”了吧,不悉心准备,亏待的可是自己呀。这样子想着,也就自然得觉着忙着安心,忙着乐呵呵的了。当然啦,大四的孩子了嘛,弄懂了什么才是革命的本钱,也就不会像当年考大学时一样把一整天都扑在文献典籍上,茶余饭后闲来无事也爱图个消遣,看一些他的诗文,权当作是在给疲惫的身体吹一阵温柔的春风。
他,算不上遥远,甚至可以说是很亲近,至少在我们这个系里是这样的。不过,经常地在窜系的忐忑和满足中能听到从别的系的同学口中说出的类似“你别唠叨了,喏,给你本诗集看看,这可是咱校中文系的校园诗人写的呢!……”之类的令人窃笑的话。看来,他真的算不上遥远,或许更确切地该算是到哪儿都很亲切吧。只是,他们不知道他其实叫文,也不知道他除了写诗歌,还写小说和美文。
但不管是系里的还是系外的,都情愿叫他校园诗人,或出于羞涩,或出于生疏。
我虽然和文同在中文系,可那个时候他比我大一级,自然地算不上熟识,我也就从众着叫他校园诗人。至于是出于羞涩还是生疏,我也说不上来,因为同系的嘛十有八九都认识,也就不能称之为生疏了。
[三]
认识文其实也不是偶然。
那年,刚刚挣脱了高考的缰绳,我好似铆足了性子的野马,在大学的草原上快活且满意地奔着。一切都很新鲜,一切又都如在梦寐里呼唤了无数遍的亲友一样熟悉。也许,就因着这股子莽撞和不羁,才愣是拗着命运把众人簇拥着的文硬是拽进了我的视线。
说文是众人簇拥着的,其实一点也不为过,那若市的汇报厅门口可是我以一颗钮扣为代价才勉强挤进去的。就像是钱钟书老爷子说《围城》一样,围在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大抵如此。汇报厅这人头攒动,灯火辉煌为的只是一台微末的诗咏会,而众人燃烧着的目光的焦点也只是不起眼的他,头发波起英格兰南安普顿式的沙滩浪花,前额耸起巴西高原式的突兀,个头还算高,剩下来的能让人关注两秒钟以上的恐怕也只有那似乎凝滞在半空中的目光了,旷达如沙漠里的驼队,内敛若群山中的虎啸。
心里虽然泛起了略略的不值,但想着要是现在再挤出去或许还要牺牲一颗钮扣,也就慢慢收了委屈安心地把目光贴在他脸上。他昂着的头稍稍一侧,在眼睑柔和地盖住他的视线的时候,又优雅地低下,再随着嘴唇的抿动,微微地晃着来回,似在品味一口爱尔兰咖啡。突然,他猛地扬起头,炯然的目光射穿满座的期待,浑厚的嗓音划裂厅堂的寂然,
风从林间路过
树叶为之争喋
风是在哪个方向吹
风不语
悄悄卷落一片黄叶
风是在这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掌声响起在何时,也不知道掌声停息在何时,我只是觉得自己的心绪被这磁性的嗓音,或许更确切地说是被这磁性的意蕴给吸引了,这是他对他的理想的坚贞和矜持吗?虽然彼时我还不知道他的理想是什么。
我用胳膊肘子撞撞挤在我身边的人,压低了嗓门问,嗨,你知道刚才说诗的那个人是谁吗?我本以为自己客气得挺有淑女风范了,可没想到招来的却是如看马戏团里黑熊走钢丝一样的诧异眼神。我有些受不了这样的犀利和怪诞,便知趣地走开了。可越走就越觉得心中那湾叫做窝囊的浪潮晃荡汹涌得厉害,最后竟从口鼻中喷了出来,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尽管挂着满嘴的轻蔑与不屑,可毕竟是女孩子嘛,心里照样还是存着那份敬佩,也会偷偷地去打听得他其实叫文,然后在人后羞涩地喊一声,校园诗人。
[四]
就这么喊着,丝毫不顾喊校园诗人要比喊文费时得多,一直到大三。
大三那年的秋天,还是很闷热的,天空下偶尔移过的朵朵泛着刺目金光的沙漠让我们忘却了秋高气爽的惬意和安逸。可那天下午,却意外地起风了,不大,但却已把校园里路边道旁老树上的黄叶卷落了一地,这般柔情着实让人陶醉,也让人幻想。
梦儿正酣的时候,主课的端木教授扫兴地走了进来。端木其实为人还是不错的,就是迂了点,有一次竟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和我们扯谈朱自清的悲哀。这次估计也没什么好事。再说了,他的不速而来还破坏了人家的温馨呢!心里觉得有些不快,就索性把头深深埋进臂弯里,还故意梦呓似的呜咽几声。
不过端木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抗议,只顾着往自己脸上堆笑容。终于,实在是堆不下了,把嘴给挤开了,同学们,我们今天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从这个学期开始,我们又将多了一位新同学。又是新同学!什么荣幸?八成又是走后门进来的。我暗暗犯着嘀咕,又觉得有些气了,就狠狠地呜咽了一下,端木还是没有觉察到我的抗议,继续迂他的,这位同学相信大家都认识,就是文,他……
文?怎么可能?他明明应该是念大四了呀?我就像是小孩子瞥见了会飞的蚂蚁一样又惊又喜,噌地抬起头,目光在教室里四下寻觅,却不想文高高的个子已经出现在端木身旁了。我想笑但又不敢,只听得端木说,哦,你醒得倒是挺快的嘛!这话说得带了几分善良的奸邪,我觉得脸有些红热,便又把头埋进了臂弯,在睫下的一线天里看文笑得灿烂。
说真的,这还是我两年来第一次看到文笑,很有风度。当然啦,这本没什么,但我后来却一直都记着文笑起来的样子,可能就因为诗人的严谨吧,笑也就成了一种稀罕,一种珍贵。
其实端木是还是不错的,至少他还能把文的椅子摆在我旁边。我有些高兴,但没有忘乎所以,我担心上帝对我的这一切垂青,只是因为他打了个瞌睡,他醒了之后也会把我叫醒。于是,我就怀着女孩子偶尔泛滥的幼稚去问端木,可他只是支吾着说这样的跨级调动不过是为了配合学校的体制改革。虽然这样的话听得出只是搪塞,但至少可以确定文是要和我们一道毕业了,心里也就安稳了些。
可是,文到底是为了什么才会屈就自己,下放自己的呢?我免不了有些混沌。
但话又说回来,像这样的事也算不上是最新鲜的,因为在这个当儿,校区里传的沸沸扬扬的是学校被划作试点搞按学分缴纳学费的改革了。这倒也好,反正得修满了学分才能毕业,挺公平的。再了,要是家里拮据手头紧张的话也还能缓上一缓。家里拮据手头紧张?我的思绪凝滞了下来,久久地揣测久久地担忧,莫非文……我好几次都想问他这个事,但无论是面对他激越的陈词还是他深沉的凝思,我都不敢拿钱赀的秽色在他眼前晃荡,我只是看着怜惜着他节衣缩食的每一天。大三这一年,除了几个必修的学分外,文就几乎没修什么别的学分。不过这也不算是什么不幸的事,至少他能腾好大一块时间来写他的诗歌、小说和美文。事实上也是如此的。
[五]
和文相处的日子显得很平淡,多半是他安静地写作,我安静地看着他。不过慢慢地,我就不光只会安静地看了,我会默默地泡上一杯牛奶,特浓的那种,再放上半块方糖,他嫌那还不够甜嘛,然后悄悄地端到他桌上,才坐下来牢牢地看着他。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但其实也不是很久,就是大三的那个冬天。
秋天去得很快,冬天却来得很晚,似乎是为准备纷飞的纯洁而耽搁了,说来那年冬天的雪确实很大,虽算不上有半尺厚,但一脚踩下去也能把你的脚脖子给没了。从阳台上望下,整个校区仿佛成了冬天里的童话,很安详很宁谧。偶尔地,会有一两只斑鸠在视野里闪动。该是在为它们的妻儿找食吃吧,我无端地想象着,便生了浓烈的羡慕,羡慕它们的妻儿。
有些时候,人真是得窃喜有上帝在和自己开玩笑。这般羡慕没过几天就消释殆尽了,因为文的出现让我只需品味自己的幸福,而无意于贪恋斑鸠的美满。
两个人在一起,许是为着一脉温馨,许更是出于一种合理。下雨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也就能在这迷蒙的梵宇间省下一朵本该经受风雨洗礼的伞花,失了距离,生了依恋;抑或偶尔地,两个人在一起还能为皱着眉的老板娘省下一杯已不见了吸管的珍珠奶茶,失了体面,生了甜蜜。两个人在一起,似乎眼里就没了电闪雷鸣,有的只是虹霓;两个人在一起,似乎耳畔就没了鸡鸣狗吠,有的只是鸟语。
可是,渐渐地才觉得,文懂的是情趣而不是浪漫,他会把鲜花称作姑娘,却不会把姑娘称作鲜花。心中的嗔怪虽免不了,但也只不过是些许的,不至于泛滥,我也仍旧给他泡上一杯加了半块方糖的牛奶,坐下来看他写作,只是已不那么安静了,许是因着天气变得暖和起来了吧,我单是爱躁动似的瞎扯上几句,语气里也惯带了那种撒上了娇的不满,文,我想看你写的言情。
文没有抬头,我不写言情。
我有些气急败坏,也有些无理取闹,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
文还是没有抬头,我只是在体验生活,激发些创作的灵韵。
我有些失望,低低地吐字,你骗我。
文手中的笔像是断了水似的轻抖了一下,可我记得我说的是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我哽噎,把头埋进发稍,不语。
文抬起头,静静地看着我,又莞尔一笑揉揉我的后脑勺,傻姑娘……
我还是不语,只用铅笔写给他几个湿漉漉的字,我知道,风是在这个方向吹。
大海再平静也经不起一砾碎石的搅扰,起了浪涛就是最直白的绝望。我知晓曾经无数次用来熬过伤心的侥幸也只不过是一腔奢求,未来已不再渺茫,我该做的只是纯粹地去接受一个破灭的未来。可我仍愿坚持,像在大海里遇上暴风雨的船长一样坚持,为的不只是苟安,更为着一船水手掌舵时的灵韵,这该是对他们心灵的莫大安抚了吧。
我知道,我只是在坚守一种责任,一直到水手们甘愿弃船的那一天。
我们,是我和文,隔了一棵快有一米高的大叶黄杨站着,彼此有些远,远得已经够不上称我们了。良久,我和文都没说一句话,只是望着彼此,累了,就望望脚下被踩恹了的小草,再望望头顶浮着薄云的蓝天。许是静默太过漫长,我不由地开始忐忑,便垂下头在层出的词藻中踯躅,却怎也寻觅不出合适的,便想还是先寒暄了再说吧。可抬头的一瞬却不小心瞥着了文微启的嘴唇。他薄薄的嘴唇显得有些木怵,见我抬了头就慌忙地闭了起来。看他这般欲言又止,我又深深地低下了头,暗暗地消了忐忑之后,忽然觉得想笑,可又实在笑不出来。
文还是开了口,谢谢你……我是说这半年来你给我的灵韵。
我抬起头,甩开遮眼的头发,把笑容露给他看。
文像是本来就不期待我回答他什么,又多余似的补上一句,谢谢你。
我忽然觉得有些难过,便把视线从他的眸子里移出来,放到他的衣襟上。
文似乎全然没有觉察到我的难过,竟从身后变出几枝花来。我无知它们叫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是玫瑰,更不是百合。不过倒也挺美的,淡蓝中衬着几片白,很素雅很纯洁,更像是友情,欲滴的样子。我乐了,他也笑笑,把河边柳树的腰给笑弯了。
原来,文是早就盘算好了的。
就这么因着彼此心存的温存,许是关爱,许是体恤,许是顾怜,我和文都忘却了难过,沿着河安闲地走着,走着,一直走到毕业。
[六]
该是有好些日子的忙碌了吧,塘里的蛙声已很稀疏,我们这群大四的孩子们也三三两两地清闲了下来,开始重拾旧好,披着昏星在塘畔的石凳上边谛听蛙声,边不时地吟上一两句文的诗文。只是,这昔时满塘的蛙声于今也只剩这星斗般零落了,只几个不合格的还在争嚷着讨食吃。
毕业总是这么狼狈,三分磕七分碰,三分跌七分撞的。
我原本是不知道毕业以后该怎么办的。心里是早就盼着等拿了文凭就留在这城市里的,可真到了这个时候,却又怎也割舍不了那份揪着心的思楚,我虽给不了爸妈能坐享清福的宽裕,但也不忍见着他们为着也一份我给的寂寞而添染了白发。可正无所措手足间,校方竟函告希望我最好能留在学校继续发展。我也就欣然领了情,也是为了等将来日子好起来了能把爸妈从那丁点儿大的地方给接出来。
我生怕丝毫的闪失都会让自己的梦想破灭,就如期赴了职。工作,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个陌生的概念,即便不是正职,只兼了一个党委办公室的文秘,就已经把我忙得晕头转向,辩不得南北了。那漫天飞舞的文件和档案,和那种特别存于夏天里的白色,让我觉得是无比地燥热,心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在胸膛里瞎撞,耐不了这种人不得不耐的烦,我知道。
等把这一切都给弄稳妥了,我才发现这个往日闹腾的校区已近乎是人去楼空了,我生了些许的感伤,但我无暇顾及,我想到了文。我惴惴地敲了两下门,很轻,轻得似乎只有自己听得到,但门还是开了,只是开门的是文的室友。望见文的床上是那般的空空如也,我像是完全忘了礼数,寒酸地问,文……他走了吗?
没!没!文只是去买火车票了。这是一个声音,难以用任何词藻来描绘,石虽然还没有触及海底,但它分明是在下沉。
这天的夜色美极了,紫蓝的,像是鸡尾酒,令人陶醉;月亮也只差一点就满了。我和文徜徉在校区的曲径,也还是良久的静默,就像一年前那样。但这次是我先开的口,真的要走吗?
是的,火车票也已经买好了,明天的。他回答得很干脆,不容分说。
我像是被什么触痛了似的,猛地抬起了头,望着他,又忽然把语气揉缓了说,真的非要走吗?外头不比这儿容易,就算是为了我,能留下来吗?
不。这次他显得有些迟疑,但他不怯懦。
我没再说什么。
挨过了又一阵良久的静默,他许是在告诉我他的歉疚,你要知道,我有我的理想,我要去闯荡……对不起……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想哭了,但没发出任何声,只悄悄地落了一滴在自己的鞋子上,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一个浓重的夜里,这种沉重还不足以搅扰它安详的美梦。我又一次选择了沉默,不是怕坏了这夜的宁静,我只是无端地以为,或许在这个时候,沉默是我对文最深的理解。
月色还没有把树影晃动多少,这一夜就这么结束了。临别时,文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学校里工作忙,明天你就不用来送我了。
可哪里能不去送他?我就只是这么想着便不知不觉地到了火车站。我看到文了,他正挤在车门前的队伍里,人很清爽也很精神,我也就少了一份挂念。可我不敢叫他,许是怕他见了我之后又会生起薄薄的歉疚。我只是静静地站着看着他。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里,他的每一步都显得是那么的艰难,似乎每跨出一步就是跨出一分要被这个世界挤掉的危险。待到他把整个人都安在车门里的那一刻我才有了一分安心。可真的只有一分,他那裹着理想的旅行包反被门闩上一颗蛮横的螺钉给钩出个洞来。可他全然不知,照旧背着他的旅行包朝前挤着。这只旅行包还是文上大学那年从他老家背到这里来的,五年了,不曾被弃换过,只是褪了一些本原的色。
我静静地看着他,直到眼前涌起一股矇眬,这是一种晶莹的记忆,有几分青,那是酸涩;有几分蓝,那是忧愁;有几分绿,那是憧憬;有几分紫,那是幻想;还有几分未知名的伤感。
火车开了,带着文的理想从我的视野里开走了。
[七]
生活就像是一涧浅浅的溪水,平静地流淌着,没有黄叶戏涟漪的浪漫,也没有波涛碎礁石的悲壮;工作就仿佛是这溪上粼粼的波光,赏玩了这里的,那边就急得泛滥了。
我本来是不该有任何的埋怨的,怎么说这些年来学校也没亏待过我,津贴、红利、职称都不曾少了我,我若是这般怼恨反倒显得我是以怨报德了。只是心中会免不了生起无端的落寞,特别是做了党委秘书长以来,上要和局里绕着弯子地打交道,下要忙着应酬成堆的师生资料,等回了家还得对着一桌的残盘冷碟苦笑。这日子过得就好比是被蒙了眼的驴子在围着碾子瞎转悠,每圈都一个样不说,磨的还都是一个味的浆儿。
看来谁也不曾无辜地枉做了我的怨府,我只是平白地觉得生活有如荒漠般满目凄凉,需要些调剂罢了。
又是一整天的忙碌,我正准备提起挎包回家面对另一份索然,不巧电话响了,是教务主任来的,说是有个学生党员犯错误了,要调出他的档案来看看。反正回了家也不见得能有多少舒坦,我也就没什么不乐意的,但还是懒懒地走到已上了锁的档案柜前,开锁,找档案。
世事大抵如此,你越是急着寻觅的往往藏匿得越好,而你不经意间却往往会得到那些你曾经热切盼求的。档案我怎么也没找着,报纸倒是有一张。虽然算不上有多大的纪念意义,但我也曾为它翻箱倒柜过老半天,不为什么,只为的一份熟悉,一份思念,也许这一切都归于它娓娓谈起的一丝悲哀,
我向来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俭约得最深广的民族。
自年少以来就嫌烦琐,宁叫妈妈作娘,叫爸爸作爹。可没想等上了大学,耍了两年笔杆子耍出了名声,奢靡的同学们却不厌其烦地宁叫我作校园文人,这四个字难道就不拗口吗?我开始有些怀疑我向来的固执了。却不料毕业了,外面的世界又是一片俭约,迪斯科舞厅嫌长,便改口称作迪厅;打火机也嫌长,也给改了,干脆就叫火。
但我是向来不以中华民族的俭约为荣的。
当初看到这段叹着些许无奈的文章的时候,我免不了有些诧异,这般高慢,这般脱俗,又这般嫉世,像极了文。我不禁有些冲动,急迫地找寻着它的作者,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并不是文,只是一个叫文影的,不曾听说过。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有文的风骨,在他的身上我似乎也能隐约窥到文的影子。如今重又拾起那段回忆,我竟又莫名地觉得这就是文写的。
许是因着这份难得的亲切吧,一直到现在,我都还珍藏着这份报纸,也开始关注起有关文影的一切。不过令人不得不哀叹着苦笑的是,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哪一份期刊上看到过他的文章,哪怕我跑遍所有的街巷翻遍所有的报纸和杂志。
[八]
但日子久了,曾经有过的钦慕或是恋念也就自然地被碾磨得灰飞烟灭了,就连这座曾经万般向往的城市也竟被我惺忪的睡眼看得如同摇篮一般,这等安逸是如此地让我恹恹欲睡。不过明天倒好,能到省城去开会,虽然这段将漂泊异乡的经历尚花不了一天的时日,哀怨是有的,可只要一想到能感受另一份新奇,内心也就被久违的兴奋给满溢了。
可这天实在太热,不停歇地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途,到了省城又连着换乘了两趟公交车,所以人感到特别的难受,胸口也好闷。终于耐不住了,离会场只剩最后一站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些想吐了,就开了窗,换换空气,也为着不时之需。可没想我这一无心的举动竟招惹来了报贩子的一拥而上。自打上大学那年体验过这种拥挤的场面以来,我至今仍有些许的后怕,甚至于惶恐。这种想法驱迫着我硬是忍着不舒服要把车窗关上,却不料这当儿竟给一只刻满沧桑的手给逮着了,随着这手塞给我的是一份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我惊诧于他的勇敢,也钦佩于他的勇敢,就低头寻了钱要给他。可等我抬头时,我却看不见一双向我期待生活的眼睛,我也无力去探头搜求,只呆呆地捏着钱,未料想几行用快断了水的钢笔写就的湿漉漉的字却让自己的心灵为之触痛,
风从林间路过
树叶为之争喋
风是在哪个方向吹
风不语
悄悄卷落一片黄叶
风是在这个方向吹
我慌忙探出头去,才见一个高大的背影在车间窗前穿梭。我不然地回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在那个永恒的深夜里。我不免觉得有些可笑,可我的面容凝固了,我无法流露出对他的丝毫亵渎,他毕竟是在闯荡,他毕竟坚守着他的理想。而我呢?似乎只会把自己的腿脚蜷缩在这现代文明的冰凉躯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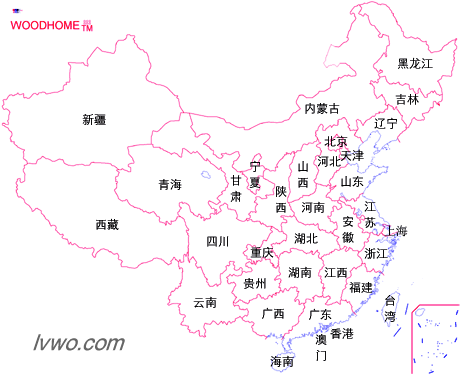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