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我的老院子了,就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近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沾染了老院子的不少光晕。院子不大却承载不小,除了岁岁枯荣的草木,光阴还留下了一些梦想的痕迹和亲切的呓语……
1.树会记住很多事
在我的老院子里,我觉得没有比树们更有资格发言了。树是老院子最忠实的朋友,我们一家有大半时间奔波在外面,只有树们守在家里,被几个坚硬的锁子锁着,只把它们长长的手臂招摇在墙外边。人们都说,院子里树太多了,光线都让树遮完了。
的确,四分地的院子,两个苹果树,一棵李子树,两棵桃树,一棵梨树,一棵杏树,一棵葡萄树,还曾经有棵花椒树,被我伐掉了。那是邻居老白再三嘱咐我的,他说宅院是很忌讳栽花椒树的。我未在意,他就扳来厚厚的县志给我看。他翻到民俗那一张,读给我听,我被他的好心感动,觉得不做出点行动似乎很对不起老人家,于是我狠心挖了它,移植到一位朋友家的果园里。
在我的院子里,树占据的空间比人的多,朋友们说有点喧宾夺主,还有些鸠占鹊巢。他们的话也对,每逢雨季,院中潮湿,砖生青苔,有点江南院落的感觉。我也曾有过伐掉几棵树的想法,但伐哪一棵呢?李子树吗?它是最繁茂的,它伞一样的树冠完全遮住了太阳,有几棵还把它的枝条扯到了屋顶上,风一吹,几页瓦被掀了下来,摔碎了。伐了它吗,不能,在院子里,它是最让人割舍不下的。还是春寒料峭呢,树们刚钻出点嫩芽,它就把一咕嘟一咕嘟的花缀满枝头,成为方圆左右的一道美丽的风景,麦子刚刚透黄,一树的李子就开始泛红,它的早熟、它的甜蜜,赢得了朋友和亲人们的喜悦与欢畅,渗透在孩子们的记忆里。说要伐它,孩子们首先反对。我一直感觉树是会说话的,它们不但有生命,甚至有感情,李子树是院子里最老的主人,房子刚刚落成,窗户玻璃还未安上,我们还没有进来,它就被我们栽在了院子里。那时候的它,还是手指粗的树杆呢,八年光景,已是亭亭如盖,壮若碗粗了。
那么,除了李子树,再大点的就是梨树了,梨树是树中间开花较迟的,也是最娇贵的,容易生病也不耐春寒。也许是因为它住进来的时候已经成年了吧,故土难离,能活下就已经不易了。梨树是从三、四里外的果园移来的,那是父亲一手拉来,一手挖坑并亲自栽植,一年一年侍弄着长大的。那时他移来两棵,一棵没有活,只有这一棵存留下来,在某种意义上,它和我一样同为父亲的孩子。即使父亲在把家搬走后也还是在一直过问,长得怎么样,花开得繁不繁。然而它总是很不幸,第一年花刚开罢就遭了倒春寒,幼小的梨落满一地,其状甚惨。第二年花更繁,刚刚把好消息告诉父亲,不料一场疯狂的沙尘暴,让残英遍地,其状更凄。随后几年也许元气挫伤,花依然很繁,最终梨长得很大了,却都一个接一个地凋落了,即使存留下来的,也全部从心里面坏掉了。仔细地想想,自从父亲在它的旁边挖过一个大坑上过回粪以外,我再没有施过肥,而且它一直被夹在两座房的背阴处,阳光不是很充足,让它结果怕是很难了。但让我去抛弃它几乎是不可能的。父亲退休后,搬到了市里住,回来的很少,加上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看着这棵高大的梨树,我就能想起父亲把它移回来时的情形。对于父亲给予它的付出,它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借着微微的轻风讲给我听。我也在同样的夜晚,在昏黄的灯下,静静地倾听它的心声,就像所有的孩子对他们的父母的绵绵的思忆。
其实最易遗忘的要算桃树和苹果树了,他们都是朋友从他的园子里移来的,苹果树也怪,我很少管它,却果子一年比一年繁,年年结果,枝头压得很弯,但品质不好,是那种老品种秦冠。桃树是那种油桃,结在最高的枝头上,摘一个很不容易,加上味酸,倒牙,都自生自落了。邻居老白一直念叨,这娃娃和别人不一样,嘴不谗。说起谗,妻最谗的是杏,所以一年她最关心的也是杏树。其实那棵杏树是她吃过的一个杏核长出来的,妻把它移栽到房侧的宽敞处,并嫁接了别的品种。年年杏子不多,却很大,很甜。看着它吃杏子的样子,我就想起妻和我恋爱时,满山去摘酸杏的情景。此杏子而非彼杏子,但杏子真的会告诉我很多事,我们被事业和匆忙的生活追赶着,静下来想一想杏子,想一想往事的日子的确不多,生活一如流水,筛掉了许多东西,也冲走了许多东西,是啊,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什么都来不及准备,许多的日子就山一样地涌来了。在流水般的日子里,许多很细很细的细节我们都忘记了,而树们却一件一件地替我们记下了。
2.同居的朋友
老院子寂寞又不寂寞,寂寞是因为院门常常锁着,只有周末才会响起一些欢笑声和喝酒行令声,因为安静,因为与邻舍的互不干扰,我的院子成了为生活和工作所累的渐入中年的朋友们抒发情感和宣泄情绪的好所在,我也因此落下了热情好客和人缘不错的名声。我曾在某个春节拟一副对联,书于门户,曰:鸿儒谈笑间,白丁往来处。其实岂止白丁,连四脚、毛足、拖尾之流也闻风而至,成为我的同居之友,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矣。
记得那一年一个冬天的夜晚,孩子尚未出世,怕冷的妻脱衣上床,爬在床上看书,我趴在桌前的灯下写东西。忽然妻“咦?”了一声,她发现枕头竟奇怪地忽闪忽闪动起来。她用手一扯枕巾,不由惊叫一声,一下子裹紧被子,比老鼠还快地坐起来。我看到一只小老鼠正悠然自得地在枕头上玩耍,看来妻的惊叫并没有吓住它。我用条帚去打,它才“吱”的一声逃掉了。妻因此害怕不肯入睡,并由此抱怨老院子的种种不是。事实上从那时起,老鼠已经在伙房里成群结队了,他们在菜篓里、油瓶、菜坛上肆无忌惮一番后把一堆又一堆的“纪念物”留在砧上,每次做饭,妻都要反复地清洗好多遍,一边清洗一边把对老鼠的仇恨转嫁到我身上。这时候,我就戏噱,这说明咱人缘好,不仅人气旺,连鼠气都旺呢。然后许诺一定卖些鼠药来,以解她心头之恨。然后就像好多话,只是说说而已,却未真兑现过。直到那一年,流行鼠疫,死了不少人,我才真正害怕起来,终于备了药,杀死了不少肥胖的大老鼠。
要说害怕,鼠还在其次,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两次看到了蛇。在光滑的水泥地上,蛇打滑前行。原来它离开了草丛的附着,竟是这样的笨拙不堪。虽然它没有袭击我们的意思,却让我真的很害怕,谁让它长一副凶恶相呢?邻居家的大男孩用铁锹把它挑出了院子,然后我仔细地堵塞了所有的水窗眼。还有一次我不在,一条大蛇却撞在了妻的脚下,她惊慌失措,叫来了邻居老白,把它撵进了我家的炭房,妻搬出我的酒,在哪里洒了好几瓶。好长一段时间,炭房成了一块禁地,妻杯弓蛇影,看到一截塑料水管都会失声尖叫。我也终于担心起来,尽管朋友从迷信的角度说,家里进了蛇是件好事,但毕竟家中有孩子,万一遭遇不测,岂不罪莫大焉。然而,惹人担忧的不仅仅是蛇,那日妻揭门帘时突遭毒蝎袭击,手指红肿,由失声尖叫而泣不成声。从未见过大人哭泣的女儿竟不适时宜地笑个不停,并从此成为她的笑柄,那壶不开提那壶地说笑。
奇怪的是,无论老鼠、蛇还是蝎子都撞在了妻的身上,却与我无缘,然而那晚的一幕却凭添了几分我对老院子的神秘感受。那是一个月光如水的子夜时分,我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离开书桌,来到院子里小解,忽见月光下院中的石桌前蹲有一物。我于惊悸间揉眼细看,乃一红狐,其神情自若,面庞清瘦,双眼有光,长尾拖地。我以为眼花,跺一下脚,它竟愣了一下神,不慌不忙、迈着很像是那种细碎的步子顺墙根而去。我撵过去就再也没有看到,因为后墙根有个很大的水窗眼。我站在月光下,身上的肌肉不由缩紧,我才感到了害怕,进屋紧闭房门,硬是把妻从睡梦中拽醒,告诉她此事。她说狐女深夜来访,我是有了桃花运。在对动物的人性化审视中,我一直感觉狐是有些媚态的,这种“媚”连同“娇”、“妖”等字眼所描述的边缘化情态很奇怪地就构成了一种迷人之韵。也许常做狐梦的蒲生亦心有同感吧。朋友们闻说,告诉我毗邻庄稼,什么野物都有,平日里要关好门窗。红狐的造访,让我的院子有了几分梦幻的气息,然而以后夜深人静,除了时有猫头鹰惊醒熟睡中的妻,我却没有再见过红狐的影子。
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院子与自然界相融之故吧。春天,果树迎着暖风,长出绿芽,满树嫩黄的小星星似的花朵,像一团团粉嫩的绣球。院子里泛起潮湿新鲜的气息。墙边的黄花草郁郁葱葱,摇曳的花朵风神楚楚;细长的葡萄蔓把婀娜的身材伸出墙外,临界掠鬓,逗引路上经过的孩子;所有的生命都亮晶晶的,所有的生命中都仿佛流淌着一条条纯净的小溪。我下班回来,将自行车骑进幽静的小巷院路,把双扇的木门摇得吱吱勾勾。而后墙后面,又会传来农人吆喝犁地的甩鞭子声音。在这自然界的无限风光里,难道除了我才有享受它的权利吗?在院子十分岑寂的时辰,我常常听到一些仿佛喁喁絮语的轻微声息,细细在花丛草丛中察看,竟是些可爱的小蚂蚱、豆虫、蟋蟀和膀大腰圆的蝈蝈,还有无数忙忙碌碌的蚂蚁。这一隅之地,就是一个完整合谐的世界。在院子里,我不寂寞,我能找到心灵的悸动与大自然的声息完全合拍的感受。
我离开了院子,树已经属于别人了,老鼠、蛇、蚂蚱、蝎子甚至红狐都成了别人的故事。我站在楼房的阳台上,眼前除了人群还是人群,耳边除了车声还是车声。不过,我再也不必担心出差的时候,妻为蛇所惧,为蝎子所惊吓了。
3.邻居
比邻而居者,谓之邻居。院子空旷,没有老年人守家,就更显得空旷。我们这一片全是老年人,退休的,或接近退休的,他们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闲散自在,只是有了孙子的,要按时准点去幼儿园接孩子。但那也是一种放风和活动。老白就有两个孙子,整日里缠着孙子转。
在院子里十年,老白很让人难忘,自从那次窃贼登堂入室光顾了我家之后,老白就一直自责,说他没有给我们看好门。从此我们外出,回家来大门一响,无论多晚,他都要披衣出来探询。每年春节,我们一家都要上父母身边去过,所以看门的差使就交给了老白,想起来这几年多亏老人家。这种很纯朴的邻里之情,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动。
我们一家恐怕是这一片最匆忙的,晨起昏息,像只被光阴的鞭子抽着的陀罗,只知道按照既定的路线旋转。也许老白他们都是从我们这个年龄过来的,所以知道我们忙什么。老俩口每天很早就起床,打扫他门前的时候,就连我家的门前都扫得干干净净。当他的扫帚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还在睡梦中。出门的时候看到整洁的门口,就暗暗惭愧,下次一定要亲自扫,而且要将隔壁邻家的门口都打扫。然而,等到我起床,老白他们已经将门口打扫完了。每当我对老白讲起,他总是说你们忙着干事,辛苦,这点小事,他们顺手也就干了。
老白是干林业出身,所以侍弄果树很有一套,同是李子树,他院里的结果就特别繁茂。同是梨树,我家院子的就老爱生病而他家的却果实累累。快发芽了,老白就说,枝条要修剪,我来帮你剪,然后就登高攀低地给我修剪。快开花了,老白就叮嘱,该打药了,树上有蚜虫了,而且给他喷药时总要展过墙来把我院子里的树喷一喷。我们相隔一堵矮墙,颠起脚尖就可以望见各自的院子,我们虽然很少串门,但总是隔着墙拉话,借东西。他总爱问的话是,最近听说要涨工资了,退了的人是啥政策?我总爱借的东西是他的喷雾器,不知怎的,我买了好几个,总坏,而他家的老用那一个却总是不坏。我就想,看来一件东西的寿命在于它的运气,就看它碰在谁手里。老人牙痛,常常彻夜难眠,我从小患龉齿,牙痛伴随我长大,故而我知道牙痛的滋味。有一种叫卡马西平的药专解他这种神经性的牙痛,而我们这儿却买不到,所以我出差总要给他捎几瓶,他很高兴,说是我常常让他做好梦。看到他的高兴样,我也感到很快乐。能让一个人常常做好梦,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呀!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原本就应该这样,在给别人哪怕一点点的帮助和带给别人哪怕瞬间的快乐,都是一种幸福。由此我常想,人们常常抱怨,这人对你怎样怎样不好,那人对你如何如何。其实仔细深究一下,别人对你的态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你自己。或者来自于你本身的缺点,或者来自于你对别人的态度。
我终于离开老院子了,老白的隔壁的门锁了好长时间,多半年不见老白,某日忽然碰上,异常亲热,说今年李子树上花开得好繁。回去说给妻,妻说有空了过去看看老白,邻居一场不易。我住上了楼房,我知道我再不会有这么好的邻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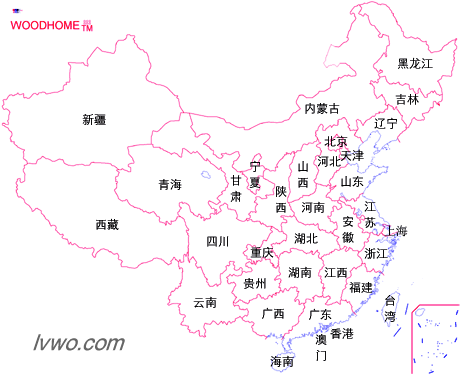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