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时翻以前的东西,看写过的日记,感觉时间真是一双无形的手,捏就一个个有形的感觉,我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映射到日记里,组合成一幅幅简单的画面,我不会写小说,也就只能自然而然的淡淡的述写,我写几个主要的画面与几个主要的人,他们是模糊的,他们的模糊就算是没有我模糊的文字也清晰不了。
一直很想把自己高中最后一年的生活写下来,就当是一个个断点也罢,但我高中最后一年不是高三,而是高四,我不可能理会大多数人的不解,也犯不着为过去悼念,我过着自己的生活,就如我写自己轻描淡写的岁月。
岁月轻描淡写,故事轻描淡写,人也轻描淡写。
那年的夏天特别漫长。感觉像枯草一般,疯长后日暮西山,却又似乎死灰复燃,常常是一个人坐着发呆,那时侯的景色不美但月亮总是很亮很圆,后来开始试着吸烟,觉得弥漫的烟从自己身边散去的感觉很好,像腾云驾雾,再后来慢慢习惯点着烟,搁在那,不抽,以为境界很高,希望让一种东西消散的时侯另外的许多东西也跟着永逝,像烟和时间,或者生命,还有地球,二个月,生命从十九岁走到十九岁。但总该得有些东西己经无可挽回,或者,得从新开始,我知道。
我是在十月中旬才走进复读班教室的,那时学校己开课一个多月了,我坐到了教到的最后一排,靠着窗,向光性很好,也可随意看外面的风景,窗外面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池塘也是风景,包括池塘里的一切。上课的大多时间,我总在纸上写些乱七八糟的字,或是一个看着窗外面沉思,有时也睡觉。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睡着,猛然觉得有人在敲桌子,抬头看到一个目光深遂的老头正向背后走来,我急忙拾起笔,摊开书,当那个晃动的身影折回讲台时,我侧过脸对同桌报以感激一笑。
你可以叫我小风以前的同学也是这么叫的,我说,他也笑笑,递过一张纸,张文,我轻声念了念。课后那个叫张文的同桌微低着头说出去走走么怎么你整天不说话呵,你看这背后一排可就只有你我两人,挺感性的笑笑,说没啥说也不想说于是不说,看了看窗外的池塘,水是深绿色的,死寂死寂,心说原来这水,这池塘,也这般的失落,像人一样,转过脸时,张文己没有了踪影,看了看左边,最后一排真就只有两个位子,想想脑海里张文印象是架幅深度眼镜的书生样,文弱文弱,无聊着,拣起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我们这一代,生不逢时,却横冲直撞地,奔向人间,最终只落个,头破血流。”
看了看 ,觉得有点什么,嘴角一弯,笑笑,右手撕下,揉作一团,换到左手,很自然的落到地上。
池塘那边是一条连着学校大门的路,无忧无虑的许多人,一簇簇,一群群。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快乐是他们的,与我无关,或者明年今日,他们当中也会有人这么想吧,翻了翻桌面上的书,脑海里一片模糊,这是记忆中的第一幅失落的画面,我也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失落的开始。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只是人变得愈发的郁闷和敏感,走着路也在想人生的沉重与生活的旁徨。开始间隔地去上网聊天,很多时侯,总眯着眼睛任手指敲打着键盘,然后睁天眼凝视着框中的一行行字,带着一脸无奈又玩弄的表情,净是冷漠,净是嘲讽。
除了向过去的同学发点自己后悔与失落夹着愤闷的感受外,基本上是在和一些不知天南海北的人胡说,心情好时会说自己在洛阳城赏牡丹或者是在黄金海岸漫着步晒太阳,但大多数时间心情不好,于是我便隐身在孤单地狱从爱的天堂慢慢坠落。
喜欢隐去自己真实的一切,包括表情。走回到路上,又发现自己只是虚脱的一个子人,天与地的反差,那时顶喜欢的一句话是你无须知道我是谁,和你一样,我在用手指玩弄这个人间,一遍,一遍,又一遍。
在师院学中文的同学从网上发过来一首诗其中有句是“苍天问君何所有?揽厮寒风独自孤”,不信是他自己写的但觉得挺好就写了下来。自己刚好有支出水很大的钢笔,落笔处,墨迹闪闪,很书法的味道。
那时侯时间不紧人也散漫,竟很真挚的关心起姚明和他的蓝球,更经常的是一个人伴着台灯深夜发呆,后来慢慢变成了走到阳台上去看黑黑的天,也渐渐体味了同学那句诗的意境,黑夜,高处,一个人,还有寒风。
圣诞节的前几天家乡意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班上的男的女的刹时忘了形忘了痛,在雪地里摇头摆尾在己十几年没有见到的景致里畅快淋漓,告老返童,教室里很空,我便看着窗外的雪和池塘,雪花迷迷糊糊一沾水便又还是水四周都是白色,池面便显得愈发的绿,很闷 身边的张文又不知所踪,于是我更加寂寞和无聊,转回头竟和一女生的目光想碰,脸热得不是很自在低头写起了自己的字来,心想在这里人们真的是不敢要浪漫的自己脆弱的心灵己容不得再伤几份自尊但还是勉不了有种窃喜又嘲讽的想法,背后就是墙难不成她在谱白色恋歌?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笔下的字却是:曾观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忍不住想笑,巫山云雨巫山云雨,看外边那些大约己忘我的人们,沉沉的心也在下坠,眼睛很痛,微微合了合,又是心烦意乱。
哎,瑞雪是否一定会兆丰年,
开始回味一步之差的悬殊,很害怕光阴似箭因为很害怕自己一下子就老去,而没有留给人们一点可能暂绶记忆的东西,九十九度的是水一百度的却是汽,一步之差。
小麦的出现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关糸开始于网聊,本来都己经三四年没有见面的同学,该是很适度和言语朦胧的,但由于一些至今也不记得的话,一下子感觉便变了许多,我说我只记得你是文文静静一个人,她说你那时也怪老实的,我又说我现在也很老实而且老实得无比空虚,她说她己不再文静却依旧十分无聊,她不说我为何会空虚,我也没问她怎么会无聊,感觉熟知,又老道,我不知道小麦是在嘲讽我还是在安慰我,只是觉得自己很满足的样子,况且一切又是那样的模糊和意味深长,那天晚上很安乐的睡在床上,却睁着眼莫名其妙的在想自己是否和她该离得很近,因为无聊和空虚的差别本来就不大,叹了很多口气,最终才幸福的睡去。
习惯在时间中慢慢沉淀许多事情也仍不置可否的执着,书上说人在很无聊的时侯容易做起件事情并执着起来,开始相信,但同时也很怀疑自己所执着的东西,听歌吧,尽管常常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但依旧一如即往的喜欢校园民谣,听老狼和水木年华,感受其中的沙哑沧老,忧郁与那份可爱和简单,很多事情都只有自己经历过来才能有些让人觉得真实的东西,我想他们是对的,他们都走过冬季校园才扣动着许多人所共鸣的弦,我想当王阳变成老狼时他与如他一般的许多人都在体味着同桌的你或她。清脆的红棉吉它,忧伤的布鲁,斯属于别人又属于自己的声音,有点时侯真的想哭,人总是放不下心的里的很多东西,而不是很镇静的问其值与不值,当所有一切都己看平淡是否还有种坚持还留在心间,物有所属人有所归而心常常不知所至。
想很努力的做事却依旧原地踏步如人家所说想要出众却怎么也告别不了平凡这是否和命运有关,于是有时侯就想活着与生活大约真的不需要太努力可总是在冥思苦想之后感到快理清个中玄机时脑子就忽然又一片模糊敏感的直觉告诉自己不要太过牵强会来的总会来不能做的就不要做该面对的终归是会出现或喜或悲,就如下一个七月。
在元旦要放假时终于知道了下雪天与自己目光相撞的女生的名字叫赵湘远,她的座位在最前排,上课时我绕过一簇簇高高低低的头窥视前方,心虚虚的,有种小偷的感觉。之后我给自材高瘦赵湘远的评价是蛮有气质的,后来想她给于我的初印象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后来的审美观而不是另外一个人----小麦。
有意无意的眼神搅得我不自在,但她似乎很心安,
都说一个人不寂寞想一个人才寂寞我倒是宁愿长久的一个人寂寞下去而不是去想另外一个人,罪恶因为背后的许多责任恐惧,接下去的后果,想想自己是背着失败一不甘心来到这里的,而她也该一样。在散漫又空虚的日子里滋养了许多不知该不该叫爱情的东西,尽管是在高四似乎没有人因此而自责或困惑他们都很幸福,我想这与快乐一样都与我无关,尽管不舍,但我更会坦然于长久的相安无事因为一天与一世毕竟相差太远,管它是青春苦短很悲壮的想以为伟大。
平安夜里不觉得有所特别,有人放了几串烟花我便又开始抚弄自己都认为晦涩的文字,心想是意境文学其实什么都不是,更好的该是没有格式的诗,拾起笔信手写了自以为是诗的东西:
“离开学校的那天,院子里沉积了厚厚的一层落叶,你问,我是不是要捡起一枚当作纪念?你的眼神标忽不定的闪烁,我知道的。徐徐的风里有一个诺言要兑现,只是在彼些仓皇的瞬间,谁也没有走到谁的面前。总认为最真的光阴是从前,最美的体验藏在心间,浮沉在往事的我,怎么能记清那张纯真的脸。想知道,从不曾有的变迁,会不会因此而改变。从来没有的错觉,未经沧桑的垫言,是不是从此就湮灭”、看了看,看了又看,自我感觉良好,很卖力的分行分段以为就是什么当作作文交了上去,起名为叶子,不因为是什么,也不意味着什么就那么暮地里闪过的一个念头,心想是在游戏文字还是在游戏人间,都己经变得不再重要了。
第二场雪下在元旦过后的第三天,下在晚上,也是纷纷扬扬,躲在被子里不断的倦着身体以为就会冻死,睁开眼发现阳子也没有睡着,于是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一起等着世界未日,阳子是我高一高二高三差不多高四的同学,也一直合租着一个房间睡同一张床。
他说起他写给一个小学妹的情书我说蛮好但心里不觉得是,我说假如那情书连我这般感性的人都感动不了更别说是女生,但我之后又说那信刚好能感动我,于是我们都笑。我喜欢这种谈话方式何况天又那般的冷人又那般无聊,最后那晚是谁先睡着己经忘记也无从记忆只是清晰的记得那张窗帘的颜色是棕色的,表面是棕色的,窗户很大也关不严,是那种一个月几十块钱的房子,现在想来记起那旬不知是因为那场雪还是那个窗户或者窗帘都无从所知,或者什么都不是。
时间不紧,但学校的课挺多,一礼拜。只有星期六半天的假,而那半天,常常是在网上度过的,是因为小麦,总像约好的一样,小麦是那种让人觉得隐隐约约却又知心贴切的女孩子,至少我是那么认为的,和她聊我自己每天都看着窗外的池塘发呆时,我知道我己相信了自己一直不相信的东西,
我说:“小麦,假如我问你相信爱情和天长地久吗?或者你会永远和我走下去吗?”
“是回答这些问韪吗?”
“不是,我只是想知道回答这些问题你需要多久去考虑。”
“那你会给我多久?”
“一生。”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她很幸福的笑笑,我也很幸福的笑笑,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样,幸福只是我自己不加修饰的词而己。
那次的作文发了下来,赵湘远的作文又作为范文被念了起来,仰着头,一脸的不屑,应该是因为嫉妒,教语文的老太半眯着眼睛动情的吟咏着被她描述为细腻动人的文字,
……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宋词,心里一动,不再摇头,开始接受自己的做作,与她的引喻,并无可比的平台,
而作为课代表的赵湘远把我的作文放到我面前时,她挺戏谑的笑笑说:“老太看不懂的。”
没有言语,只是苦笑着,看自己的那两张纸上,批着的两个字:‘离题,’
张文说他看得出来我很敏感,对什么都是,他说这话时,深度眼镜背后的眼睛定定的,像看穿了一切,
我避过他的注视。想时间会很快,很快,不可能会给谁思索的机会,心里的目标在不断的动摇,本来以为在脚下的东西变得遥不可及。
阳子开始和那个小学妹恋爱,不是因为情书,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阳子说生存不需要什么道理,恋爱也就更无需什么理由,倒是我自己,开始回寻着,那些为借口而留住的生活,大学里的同学写来信,还有照片,语气像是受了很委屈似的,觉得挺优雅,照片倒是很清晰,他们都说过得很郁闷。
我没怎么说安慰的话,背顶着枕头,仰望满是斑点的屋顶,心里思索着一个叫后无知时代的名词,什么都没能长久,做着题,感觉时好时坏,也开始用平静的心对待所有的东西,那池塘和窗户与自己,成了另一个世界。
农历二十五,小年,学校终于开始放寒假,带着忐忑的心睡了一整天,我知道自己一直都是半睡半醒,许多时侯,睡着时比醒着时想的东西更多,也更明了,但那己经不是很重要,迷惑的是,家里的每个人都挺自然而很愉悦的样子对我,这样更使我难过,农村是个世俗的地方,我想父母所承受的沉重比及我一定更甚,而我更是借着他们的萌影才得己完全,熟悉了熬的慈味,但仍难以习惯度日如年的感觉,闲着时,就抱抱那可能的小外甥,胖嘟嘟的身子,抱在怀里,软软的,热乎乎的,我总是紧紧的抱着他想自己的许多事,想也许十几年后,眼下这孩子也会如他小舅一样的困惑与无奈吧。
小外甥长得像她妈妈,清清秀秀,长大后出落成一个漂亮的男生是必然的事情,看着那孩子一副与世无争的无邪的表情,孤自苦笑,哎,自己,都还只是个孩子。
在别人看来,日子总是那么的行云流水的,我也就犯不着总唠叨自己的坎坷,在异地他乡流落半年的朋友们都回来了,带给我许多过于压制的埋怨,我知道,其实他们是快乐的,他们的不快乐是因为他们不想我因为他们的喜悦而郁闷,当然,他们不知道那种刻意的融合,给我的只能是更加难过,和小麦的联糸时断时续,我也没过多的想两个人隔得不远还得用夸张的思念,她有她的生活,我也要细算我的日子,她是个独立的人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作填充自己的将来,而我不能,我把头埋在书里的时侯,己经注定我将是个落魄的人,很意外的是赵湘远在大年夜里的电话,尽管是些平平常常的问侯,她说得忐忑,我也听得忐忑,我在家里人异样的目光中在脑海里勾画着她的影子的时侯,心里很明亮,一个人遇上另一个人,只是缘而不是份,我更相信的一句话是相识而后知是在心而不在缘,我们会相安无事,就注定会相安无事,我省略了自己的表情,给予她一个很沙哑但朗爽的笑,谁都可以决定自己下一步该不该抬脚,但没有人能预料路的尽头用不用得着两脚着地,我得尽我的彻夜难眠,就如他们过着他们欢声笑语的日子,行云流水。
年初四,阳子从邻镇跑来说,老光回来了,我便一下子回想起那个理着平头叨着烟的壮壮实实的后生来,在过去他就那么的洒脱,在任何时侯,总让人印象深刻,老光给我打电话的时侯,我听得见他内心里的痒痒的声音,我想这小子大约又想找点刺激了,在以前他就是个一分钟都坐不住的人,所以当我们八个人站在溜冰场旋转的灯光下时,我感觉混浊的音乐里面将有一个人的脸变得铁青,有节奏的拨人心弦的动感舞曲,溜冰鞋划过地面滋滋的响声,我们一色的黑外套,一长排的列在那里,老光对跑过的一个红头发的小个子耳语几句,那小子挺兴奋的划向涌动的人群,人们还是没有因为忽然有了一群不速之客而淡落心里的兴奋,不一会,对面长长深深的角落里走过来一个高高瘦瘦的年青人,他走到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时,忽而止住了脚步,我摘下墨镜看到了他点发白的脸的底色,便就一会儿,又变得原来的那般镇静,但再没有向前走,我终于明,好勇的老光为什么在半年之后还记得过去与他的节子,是谁找我,他挺自在的四周望了望,声音有点异样的小,老光没有说话,我们不紧不慢的走到他的面前,他背后忽地围过十几个人,红的黄的头发并没有遮住他们的稚气,那瘦子嘴角渐渐的涌现一股蔑笑,一缕头发从他的额头挂下,像电视里的某个画面,确实,他是个很会耍酷的人,我心中暮地一堪劝,用胳膊支了支正要向前走的老光,走到那瘦子的面前,是我,我微皱了皱眉,定定的看着他,我们相对论距十厘米,我怎么了,他往后退了退,这是个怯懦的人,我嘴角划过一道笑,身后走过两个人,拍了拍他的肩,我抬头扫视了他背后那一群人,然后,听见有人嘶、声叫了起来,、混在跳动的音乐里,在阴暗的场子里不断的回旋,走出门口的时侯,我待意的回过头看到了那一缕头发下的两股血,是浊而有腥味的血吧!
国道上,我们迎着凛冽的风,尽情的发泄着心里的沉闷,混浊的血。混浊的人,老光不时的回过头来对我大声说着话,酒气顺着风。浓列的扑向我,但转瞬即逝,我扶着他的肩,在摩托车上,那晚,我想他是醉了,我们都醉了,连同那个夜晚。
春节过后,再到学校,便和阳子商议好各自去找个房间,以便偿试一下一个人的清静会不会更适合两个人的慵懒,我很尽心的为他搬东西,他也挺卖力的为我布设房间,我说以后我们就得走亲戚了,他说是呵,到我那时可别忘了买点礼物,我大声的笑笑,其实心里都挺明了,开初一段时间,肯定会有许多不适应,或都说留恋,毕竟,阳子与我同铺睡了那么些年头。
我的男房东是一个小学校长,但女房东好像是个过于精明的妇人,阳子和我搬着东西上楼时,她便用一种很冷漠而挑剔的目光盯着我们,她问我是哪个班的,我没敢说自己是个复读生,她说她女儿也在上高三,我含糊其辞的回答着,没有理由去理会太多的东西,稍稍细心打量了新的环境。小屋,阳台,对门走出两个女生,说是应届文科班的,我笑笑,想着她们都戴着的深度眼镜,估计以后度数还会加深,想着要面对的诸多人等,叹口气,那种沉重,走不出。也解不脱。
我便开始了自己在新的一个环境下的生活,我住三楼,而三楼也只住了我和对面两个女生还有隔壁一个高一的男生,一楼二楼都是房东住着的,二楼的门好像从来都没有看到开过,估计是在里面联通着,我每天从房子背后的楼梯走上走下,极少会看到房东,这样更好,自由自在,而且,每次看到那女房东,自己便会有种被宿小的味道,怎样也习惯不过来,但好像挺眼熟,只是难以想起什么。
教室前面竖起一块倒计时,心底里便尽不住的一阵子一阵子的抽搐,慌慌乱乱的看着一张接着一张的模拟试卷,瞳孔放大,躲在最后的一个角落里,睁眼眯眼,黑色里面白色的字迹渐渐的模糊,周围开始有人下象棋,起初是几个人,慢慢的蔓延到后边一大半人,忍不住的伙在一起,神情暮然,犹如真刀真枪的在楚河汉界斯杀,似乎每个人都闷得实在不行,、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绰号叫“萨达姆”的师兄,长我们一届,但在彼此都己没有情面的环境里,己没有人再乎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可耻可恨,高四高五在他眼里,也只算是一点儿轮回,意念中的劫数,正因为他的出现。下棋便成了一种演义,我与他一局接一局的下,输多胜少,但仍不思进取,他也乐意和我对局,用他的话来说,我是这团人中最聪明的一个,言语高傲又不屑,承让别人的受用,让自己更上一层楼,自边的张文又总是一脸沉思的看着我们走每一步棋,但他自己却从不,“萨达姆”说他是在坐禅,他也无动与衷。
诚然,我与大家都挺佩服老萨的那手棋艺,但又佩服不了他那身人气,当时听得最多的话就是倒萨倒萨,禁不住的想起电视画面里不间断的枪炮声,一张坚毅的又沧桑的脸,一堆堆冒烟的虚废,一群如狼如虎的钢铁怪物。
哎,血肉模糊,断臂残垣,
断臂残垣,血肉模糊,
生活过得有秩有序却又好像很不可理喻,每天在闹铃声中醒来,在绶绶的民谣声中沉沉睡去,心思怀旧又恐惧,为了一首《你的样子》买了一盒《时间的味道》不敢綦维太多的东西,只是喜欢里面挺怀旧又忧伤的调子:梦里传来谁的声音,告别哀伤时的眼神,不明白是你为何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又不间断的听水木年华,挺深远的倾诉,像碎一块松松的泥团,铿强,果断,又不厌其烦的冗长,每日黄昏时开着窗户,把头抵在书桌上,任霞光纵情的照过自己的头与背,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到背上有点烫烫的热,起身,骨头便酸酸的,像什么利器刺穿了自己,痛苦又疯狂。
城南有座塔,依山傍水,小麦总是一身白衣站在小山的最高处,任风吹拂她,飘逸又张扬,而我却对着那山下的河,透过塔的侧影看河里干涸的水,真像死水,以前塔顶还有棵树挺高,但后来倒了,修了个圆顶。感到塔便矮了许多,水里更是倒不出任何影子,污浊的水,污浊的城市,却有如小麦这样一个清水芙蓉般的女子。
我越来越感到和小麦己无话可说,确切的说是不能说,她一脸很不在乎的样子说她工作中的人与事,我会一直沉默,也许自己,真不该去理乱她原本好好的生活,她有著令人羡慕的家世,令人羡慕的工作,而我呢,最社会最底层挣扎着还挺摇摇欲坠的无名小卒,有时都会莫名其妙的怕见到她。
你什么时侯能送我到家门口,她总是这么说,我说那样你不好,还是不样了吧,她便是一脸忧怨的表情,我想其中一下有些敏锐的东西,可自己,当初为何就要那样呢,隐隐约约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痛楚,但还是尽可能的坦然而对,想总该有天小麦会彻底放弃她那份本就不该拾起的情感,也许那话她说起来会更让我好受。
故事,一切都好像故事,淡淡的,没有描写一点儿细节。真正的淡淡的,只有一个开端。或者说,当就有一个开端时,便己有了些不详的端倪,等不到结局,却都心知肚明。
窗外池塘周围的杨柳一茬一茬的抽出了新的枝条,地面上的草更是刺眼的绿,微微的闪,春寒料峭,但倦不起身子,几次考试后我己厌恶自己一本到二本之间半死不活的成绩,老师说的轻巧,同学说得轻巧,我更是愈发的沉闷,赵湘远给过我一张纸条,只写了自重两个字,我心地里有点不屑,但还是忍不住的在意,这个平时没有说过多少话的人,我强近迫自己把笔一直抓着,那样,心思才不会走得太远,直到不久后,赵湘远作为六个复读班里唯一的一人选进了零班,我才明白那两个字中另外的意思,也不得不为自己郫微的想法而惭愧,时不时的在教室里肓目的张望,感到人们是那般的陌生,我以为她从此就会在眼前渐渐遥远陌生,但她却在某日站到了我的小屋门前,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我只能这样问,
“我早知道,”
我更是说不出话来,
我就住来你的楼下,她脸边挂着一丝调皮的笑,继而又说,这是我家,你就住在我家呵,你来时我就知道,只不过你很少看见我罢了。
我恍然,又想起女房东的脸,那张隐隐约约熟悉的脸,还有她说过她也有一个女儿在上高三的,但我还是难以把眼前的人与那个精明挑剔的妇人联糸到一起,她说她妈平时管她挺严,今天是她爸她妈都回老家上坟去了,我才想到是清明了,我望了望窗外面灰蒙蒙的细雨,记忆中每个清明好像都是下着雨的,她天真的笑,气氛变得从未有过的融洽,她对我说起她的老家,还有她那边的清明,轻松又有趣,自己也忍不住的说起许多与时令无关的事,似乎己经从某中东西里解脱,忘了季节忘了雨。
清明时节雨纷纷,细雨透过来的泥土的气息,芳香又亲切,我把背贴在白色的墙壁上,未感到有些凉意,眼角晨的屋子与屋子中的东西,朦朦胧胧。
和几个同学走在大街上,碰见了以前应届时的班主任,我心里正思索着说什么话好时,他倒先苦涩的笑了,问过得好不好,我说还行,他就在我们的眼前,半年多不见,好似比原先老了许多,发福的身子,谢顶了的头,我就忍不住的想起以前的样子:古老陈旧的小镇,那座老师不多学生也不多的学校,还有总唠叨的班主任,总是亲切苦涩,真的是苦涩,楚残,
他有点儿逃避的味道应嘱几句,就走开了,步子有点儿蹯跚,我和同学好一阵子沉默不动,哎,其实,他以前对倔强的我们己经够用心了,并不用得著有所愧疚的,我心里说,这世上的事情,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可以左右,却好像一切都己注定,命中注定,命中注定想及此,背上还真隐隐感到有只手在操纵自己。
向左,还是向右?在十字路口边,我的同学忽而这么问,
不知道,没有人回答,
生活又逐渐的变回了从前,阳子也间或的来我那儿小坐,都说些无聊的话题,还有那个小巧玲珑的小师妹,他一副大男人的气慨说待考试完了之后再去找她,我也自然的不去追问到底是东边日出还是西边雨,赵湘远的家教果然如她说的严厉,自清明过后,她再没有上来过,偶尔在的学校看到也只是远远的坦然的笑。
每天的试题,每天的课程,满世界都好像挂满六月的阳光,不是阳光,是应该说烈日的,小麦也极少的再出现在视线里,我无语,想时间会淡忘一切的,包括她的我的表情,终于有天,我在纸上写信,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但也忘了该写给谁,阳子曾给我看过小师妹给他的信,我也很清晰的记得信未的一句话,
“我们相识过,但我己忘了你是谁,你呢?”
开初是笑,后来停住了,谁也没再笑,
五月时,开始在晚上做恶梦,脖子上挂着个护身玉符,但还是常常半夜醒来,一身的泠汗,很少再去上网,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会几个人一同去路边白色的帐篷里吃夜宵,喝啤酒,那时,常聊的都是各自班上无聊的人和无聊的事,我总会一杯一杯的喝酒,但总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抿下去,我喜欢听他们说,偶尔插几句,也是不紧不慢,可有可无。
于是我发现自己不是个很会倾诉的人,或者说别人不会懂我的倾诉,我回到我孤自的小屋后,开始大段大段的写自己的寂寞和空虚,或者躺着想更空虚更寂寞的他们,地面的两个女生,偶尔也会敲我的门,问我些数学题目,给我些七样八样的零食,在开初几次真心的拒绝后,就再也不忍心拂去他们的好意。
在她们眼中,我是个古怪的人,我想她们一定是这么想的,到了六月,更多的事情像时间一样变得急促和模糊,也似乎预示着许多的故事会没有结局,或者结局不好,小麦要去上军校,是她以前工业学校难得的几个名额,我的学校也己停课,各自回去休整,我和小麦走在滨江路上,风拂过脸,凉凉的挺舒服,但仍旧莫名的打了个冷颤,我只管低头看脚下的路,偶尔用力踢地上的石子,小麦不停地说一些稀松平常的东西,侧眼看她时,目光认真而纯明,我忽然感到自己是在做一个游戏,和许多人在做游戏。
“我就要走了,到那边先住一段时间,你也要考试了。”她说,说完就沉默了,我脑海里晃过一座陌生的城市,记得她说过她有个亲戚在那边
我沉默,她也沉默,
我们就那样肩并着肩沉默的走着,走到终于没有路延续下去的时侯,她跳转过身子说她走了,
我说好,然后她就走了,
我木木站着,感到周边的天空在回转,回到了黄昏,暮色沉沉的,毫无知觉的压了过来,
心思复杂得不想想任何事情,把屋子收拾了,对面的房间,传出的是一个叫阿杜的男人的嘶哑的煽情声,叠起那些来往的信,不想再去看,尽管不是秋天,但那种氛围却比秋天还低落。
回了一躺家,谁都没有去点破隐约着的担扰,小外甥不停的在床上爬来爬去,抱着他,胸口传来渐渐下坠的阵痛,他们塞给我钱,平淡的叮嘱了几句,可我总是越不过那种平淡,但总是明白,又是一个六月己经到来,也想想了那句话,该面对的总会到来,或悲或喜。如果有很多路,但也不一定找得到出口,
也许结局会出乎意料,但心情永远只会是一个传说,我相信,六月的最后一幕望了是哪一天,反正是月初的那几日里,阳子和我在我的小屋里喝酒,是那种五毛钱一斤的水酒,我们用一个壶装着,大碗大碗的喝,然后,赵湘远就出现了,她看到了酒,好像很欣喜的样子,我说那是我以前的同学阳子这是我房东的女儿赵湘远,即而我又自己喝起自己的酒来,后来想人们在酒精的麻醉下是不须要更多的言语交流的,赵湘远的脸红红的,我的脸也红红的,阳子的脸也是红红的,头越来越晕,胀胀的,只记得好像满屋子的星星,满世界的酒精……
然后,很自然的离开了小屋,再然后,生命终于从十九岁走到了二十岁,很早的一个人离开家乡,就再没有过多的关于她们的消息,包括小麦,包括赵湘远,这是你十九岁里的两个记忆,而我,只有一个,阳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的窗口回过头对我说,我默然,时间是最好的药,它只会让你有淡淡的己经下咽的错觉,恍如隔世,也正因为一切都会自然不自然的消散了去,最后,也便有了回忆。
一直没学会告别,不知道什么叫告别,我把我的故事停在一个时间的结点,像一个十字路口,任们们从四面八方的聚来,又四面八方的散去,没有告别,没有人看到那样的一幕,我那些己经远我而去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是很用心的祝福他们的,我会抑住自己的泪,我会一个人在夜色里等陌生城市的最后一班公交车,我没能把更详细的故事说出来,只是淡淡的写,一个个隐慝的人,如一个个隐慝的故事,从夏天到夏天,其实我也知道其中更需要真实的填充,像跳跃的音符,但生活不应该像音符,一步就是一步,脚踏实地,也许以后的某一个刻,会看到自己瞬间熟悉的画面,但就一刹那,就那一刹那,我也会忘却,忘却那些不再应铭刻心底的东西。
我喜欢轻描淡写,我想让自己的灵魂轻描淡写,从一个点过渡到另一个点,生活的内容就如列在水中的一个个支点,这一格,那一格,从一个生活圈观望另一个生活圈,会有欣喜,会有向望,但更多的应该是不解,不敢说自己是个历经坎坷的人,但也己习惯别人对自己的迷惑的表情,我在别人迷雾的表情里,往往能读起许多曾经的伤心过往。
我一直未能让任何一个故事有结局,我想以后也不会,永远也不会,因为我只是轻描淡写,轻描淡写的岁月,轻描淡写的故事,还有轻描淡写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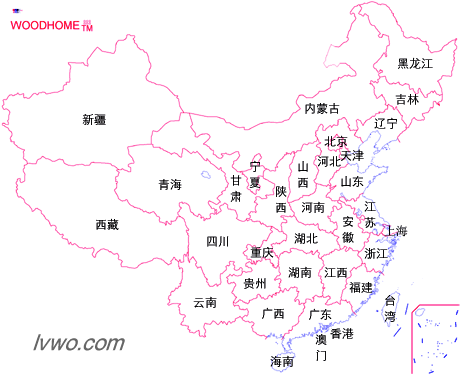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