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桥,建于乾隆二十七年。先后三易其名,初叫“南门桥”,1946年为纪念抗战胜利改称“七七桥”,1958年再改叫“跃进桥”。
那是一座廊桥,石砌的礅,木制的廊,青苔绒绒的瓦顶挤出蓬蓬勃勃的生意,写着无言的沧桑。让人吃惊的是,它竟跟美国南依阿华费朗西丝卡与罗伯特邂逅相爱的那座廊桥外观极为相似。也许这座桥亦曾连接过无数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却因为没有一个像沃勒那样倾情的作家和一对乐意透露母亲绯闻的约翰逊、卡洛琳兄妹,致使这座中国廊桥徒有其美而永远深锁在这个偏远的山谷中。
客居异乡20年了,每逢思乡,我就翻开那张桥的照片。那座桥,没有精雕细刻的装饰,木栏没有油漆,像新石器时代的石镐石钺,完全是使用功能的简单设置,正是如此,更增加了它历史的远古与悠深。
那座桥,就横在九疑山下冷江古镇的河面上。
河两岸是瑶寨式的吊脚楼,错落有序,杂而不乱,悬江而立,吊脚楼栗色的板墙满是风雨剥蚀的沟痕,青色的瓦缝,冒出丝丝蓝烟,缩缩鼻子,就能闻到一股煮芹烧笋的菜香。
湿漉漉的小巷吐出密密的石阶,像高手抹出一叠扑克,一层层汨进水面,一群妹崽子在临水边的石板上用棒槌敲着衣服,“砰啪,砰啪”的脆响在水面上荡漾,和来回的船工号子交错回旋,别有一番韵致。集市被排楼遮住,只有透过廊桥的栅栏,看到黑压压南来北往的人流,才会相信那看不见却听得到的山洪般的鸣响不是来自水坝,而是市场的鼎沸。
大约三五年,我就回一趟老家。我每次都要从廊桥上过一遍,两遍,三遍……江水依旧,木栏依然,石礅上的砖墙陈迹斑斑,而往事已然远去,昔年的记忆残象也被时代所淹没……
走在老街上,我心事重重地注视着青石板上的千古足迹,想起曾有如《清明上河图》中兴旺的古镇,须臾之间成为新城的累赘,就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当然,毫不奇怪,这种跌宕起伏是历史发展之使然,像那条冷江,没有任何坝桥可以阻挡它坦坦荡荡的流向远方。
当我走出那条阴沉的老街,踏上马路,果然是一片灿烂,一派繁荣,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与老街判若两个世界。
人,就是这么怪,我们期待革故鼎新,渴望现代生活的完美,却又对那些一去不返哪怕是落伍的东西发出声声叹息。如岁月,如生命,如祁剧,如文庙石狮石龙的残缺神坛的垮塌,如笔架山的消失,如被推土机铲平的茵茵田野……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今感慨亦然。每次回家看人老,那些曾经幼稚的漂亮的善良的面孔,都在我一次次回家,看到一条条皱纹的递增中变得陌然难辨,而新一轮完全陌生的面孔又覆盖了新的市井,出现在新桥和滨江的大排档上。乡情依旧,乡音无改,我却仿佛行走在一块异乡的土地上,用疑虑的眼光来辨认新的人群。我终于捕捉住了一些儿童相见不相识的苍老的面容,丢三拉四地掺杂在这新一轮的人群中,未知老之将至的我,只在这种情境里,才怵然发觉光阴行进的痕迹,没有任何力量能使这种行进停止下来。就像这条江水,从来没有静止一样,从来没有。
我还惦着那座廊桥。惦着它会朽落,会化作木渣,落进江心,流进海洋。于是,南门桥就由现实变成了古音,变成乾隆皇帝的故事,抗日战争的故事,大炼钢铁的故事……
那时的爷爷大概只能对孙子说:
从前,有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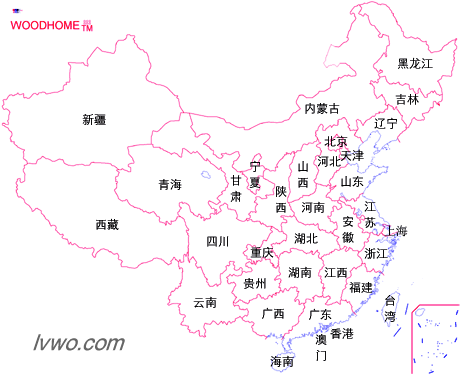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